男女主角分别是埃略特布尔的女频言情小说《刀锋(王纪卿译版)全文+番茄》,由网络作家“[英]毛姆著,王纪卿译”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我在芝加哥停留期间,由一家会所提供食宿。那里有一所很好的图书馆,第二天上午我去图书馆阅读一两种大学杂志,如果不是订户,往往是很难买到这些杂志的。我去得早,除我之外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他坐在一张大皮椅上,全神贯注地读书。我惊讶地发现,此人竟是莱雷。我绝没有想到在这种地方会遇见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抬头看了一眼,认出了我,作势要起身。我说:“别动。”然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道:“你在看什么?”“一本书。”他回答,脸上带着笑,那笑容非常讨人喜欢,使他那冲撞的回答显得一点也不无礼。他把书合起来,用他那双格外晦暗的眼睛看着我,把书的封面藏起来,使我看不见书名。“昨晚玩得痛快吗?”我问道。“痛快极了!5点钟才回家呢。”“大清早就来到这里,你太用功...
《刀锋(王纪卿译版)全文+番茄》精彩片段
我在芝加哥停留期间,由一家会所提供食宿。那里有一所很好的图书馆,第二天上午我去图书馆阅读一两种大学杂志,如果不是订户,往往是很难买到这些杂志的。我去得早,除我之外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他坐在一张大皮椅上,全神贯注地读书。我惊讶地发现,此人竟是莱雷。我绝没有想到在这种地方会遇见他。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抬头看了一眼,认出了我,作势要起身。
我说:“别动。”然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道:“你在看什么?”
“一本书。”他回答,脸上带着笑,那笑容非常讨人喜欢,使他那冲撞的回答显得一点也不无礼。
他把书合起来,用他那双格外晦暗的眼睛看着我,把书的封面藏起来,使我看不见书名。
“昨晚玩得痛快吗?”我问道。
“痛快极了!5点钟才回家呢。”
“大清早就来到这里,你太用功啦!”
“我常来这里。平常这个时候就我一个人在这里。”
“不打搅你啦。”
“你没打搅我。”他说着,又笑了,这时我觉得他有一种非常可爱的笑容。这不是灿烂夺目的笑容,这是一种以内在的光明照亮他面目的笑容。他坐在由书架外伸而形成的凹角里,他身边还有一张椅子。他把手搭在扶手上,说道:“坐一会儿吧?”
“好的。”
他把手里拿着的书递给我。
“这就是我正在看的书。”
我看了一眼那本书,原来是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这当然是一部典范之作,在它涉及的这门科学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可读性极强;但我没料到它会出现在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手中,这年轻人是个飞行员,而且还从昨晚跳舞一直到早晨。
“你为什么读这种书?”我问道。
“我很无知。”
“你也很年轻。”我笑着说。
他沉默良久,致使我觉得这种沉默令我尴尬,我正要起身去找我想到这里来看的杂志,但我觉得他有话要说。他眼神空洞,面色严肃而专注,似乎在默想。我等待着。我很好奇,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开始讲话时,他好像是在继续刚才的谈话,对那长时间的沉默毫无察觉。
“我从法国回来后,他们都要我去上大学。我办不到。经过我所经历的那一切之后,我觉得我无法再回去念书。反正我在预科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我觉得我没法融入大学新生的生活。他们不会喜欢我。我不想去扮演我不感兴趣的角色。我认为教师不会把我想知道的那些知识教给我。”
“当然,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我说,“但我并不认为你是对的。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明白,打了两年仗之后,再去当那种头顶光晕的学生娃娃,当个一二年级的大学生,确实有点讨厌。我不相信他们会不喜欢你。我对美国的大学不很了解,但我不相信美国的大学生跟英国大学生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也许吵闹一些,更喜欢马戏,但总的来说都是正派的通情达理的孩子。我认为,如果你不喜欢过他们的生活,你只要略施小计,他们就会很乐意让你自行其是。我的兄弟上过剑桥,我却没有。我有过机会,但我拒绝了。我想走出校门,进入社会。我一直为此后悔。我认为上大学本来可以使我少犯很多错误。在资深教师的指导下,你会学习得更快。如果没人给你领路,你会浪费许多时间去钻死胡同。”
“也许你是对的。我倒不怕犯错误。也许在某一条死胡同里,我可以找到符合目标的东西。”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犹豫了片刻,才说:“问题就在这里。我还不十分清楚。”
我没说话,我觉得根本就无话可答。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有清晰明确的目标,所以对他的说法有些恼火;但我责备自己;我有一种感觉,我只能将之称为直觉,我感觉在这孩子的灵魂里有某种迷乱的奋争,究竟是尚未成熟的想法,还是朦胧感受的激动,我也说不清,这种东西使他充满不安,促使他奔向他不知道的方向。他不可思议地激起了我的同情。在这之前我并未听他讲多少话,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的声音是悦耳的。它很有说服力。它像镇痛的香膏。当我想到这一点,想到他那讨人喜爱的笑容,想到他那对乌黑眼珠的眼神,我就完全理解伊莎贝尔对他的爱了。他身上确实有某种东西非常可爱。他转头望着我,一点也不窘迫,但他眼睛里有一种神态,既是探究,也是逗乐。
“昨晚我们出去跳舞以后,你们谈论我了,我猜得不错吧。”
“部分时间是谈你。”
“我想这就是鲍勃叔叔被迫来共进晚餐的原因。他是讨厌出门的。”
“听说有人为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位。”
“极好的职位。”
“你打算接受?”
“我不会接受。”
“干吗不接受呢?”
“我不愿意。”
我在介入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但我突发奇想:正因为我是来自国外的陌生人,莱雷才不忌讳对我讲这件事情。
“嗯,你知道,人们对什么都不在行的时候,就去当作家。”我轻笑着说。
“我没才能。”
“那么你想干什么呢?”
他对我一笑,灿烂而迷人。
“游手好闲。”他说。
我不禁大笑。
“我可不认为芝加哥是世界上最适合游手好闲的地方。”我说,“好吧,我不耽误你读书了。我要去看看《耶鲁季刊》。”
我起身了。我离开图书馆时,莱雷仍在聚精会神地读威廉·詹姆斯的那本书。我在会所里独自一人吃了午饭,由于图书馆里很安静,我又回到那里抽雪茄,这样可以看看信,写写信,打发一两个小时。我没料到莱雷仍在埋头读书。看样子我离开后他一直没挪窝。下午4点钟我离开图书馆时,他还在那里。我为他具有明显的专注力而感到震惊。他没注意到我去而复来。下午我有许多事要办,没有返回布莱克斯顿,直到该换衣服赴宴时才回到那里。一路上我的心为好奇的冲动所占据。我又一次拐到会所,走进图书馆。这时候图书馆里人很多了,在看报纸之类的读物。莱雷仍然坐在那把椅子上,还是专注于那本书。怪人!
1
此后我一直没有见到埃略特,直到第二年6月底他来伦敦时我才见到他。我问他莱雷究竟去没去巴黎。莱雷去了。埃略特对莱雷的那股子恼怒令我觉得有点意思。
“我曾暗地里对那孩子怀有同情。他想在巴黎过一两年,我不能怪他,我还打算替他开条路。我嘱咐过他,一到巴黎就马上通知我,可是直到路易莎写信告诉我他已在巴黎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来了。我写信给他,由美国运通公司转交,那是路易莎给我的地址,我要莱雷来吃饭,会见我认为他应该认识的一些人;我想我可以先让他接触一下那些法裔美国人,即埃米丽·德蒙塔杜和格拉西·德·夏托-盖拉德那批人。你猜他是怎么答复的?他说很抱歉,不能来,他来法国时没带晚礼服。”
埃略特面对面地盯着我的脸,希望看到他这番话会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当他看到我听了以后平静如故,便耸起了他那高傲的双眉。
“他给我的回信,用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纸头上印着拉丁区一家小饭馆的名字。我又写信给他,要他告诉我他住在哪里。我觉得为了伊莎贝尔的缘故,我得对他有所关照,我想他或许是因为胆怯吧,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小伙子来巴黎时会不带晚礼服,而且那里无论如何总会有过得去的裁缝。所以我邀他吃午饭,并且说只是个小型聚会,可不知你会不会相信,我要他提供一个除美国运通公司以外的地址,可他不但无视我的要求,还说他从来不吃午餐。就我这方面来说,他算完了。”
“不知他独自一人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而且对你讲实话,我不关心。我恐怕他是个彻头彻尾不受欢迎的年轻人,我认为如果伊莎贝尔嫁给他,是会铸成大错的。毕竟,如果他过的是正常生活,我早该在里茨饭店、富凯饭店或别的什么地方碰到他了。”
我本人有时也去那些时髦场所,但我也去别的地方。碰巧那年的早秋我打算从马赛乘一艘邮轮去新加坡,我在去马赛的途中在巴黎待了几天。一天晚上我和几位朋友在蒙帕纳斯宴饮,餐后去圆顶大厦喝啤酒。不久我东张西望,突然在人满为患的阳台上,看见莱雷一个人坐在一张大理石面子的小桌边。他无所事事地看着人们来往散步,大家在经过一天的闷热之后,享受夜间的凉爽。我离开那帮朋友,向他走去。他看见我时脸上发光了,对我迷人地一笑。他请我坐下,我说不行,我还有一帮朋友。
“我只是想向你问个好。”我说。
“你在这里停留吗?”他问道。
“只留几天。”
“明天和我共进午餐行吗?”
“我还以为你从来不吃午餐呢。”
他嘿嘿一笑,说道:“看来你见过埃略特了。我一般不吃午餐,我没有时间,我只喝一
杯牛奶,吃一块奶油糕点,可我喜欢跟你共进午餐。”
“好吧。”
我们约好第二天在圆顶大厦会面,喝一杯开胃酒,然后上街找个地方吃饭。我回到朋友那里。我们坐着聊天。我再去找莱雷时,他已经走了。
1
我以往动笔写小说,从未如此犹疑不定。我将本书称为小说,只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名字称呼它。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也不会以死亡或婚姻来收场。一死百了,死亡总是故事的大结局,而婚姻也能使故事圆满收官。老于世故的人昧于事理,才会瞧不起传统上所谓的大团圆结尾。老百姓自有健全的本能,认为有了这样的结局,该交代的就都交代了。男性和女性,不论经历多少悲欢离合,终于得以聚首,便实现了他们传宗接代的生物功能与兴趣。可是我会让读者悬于半空。此书写的是我对一个男人的回忆,我跟他总是时隔很久才会有一次近距离接触,在分手期间,我对他的遭遇知之甚少。当然,我发挥一下想象力,便足以合乎情理地填补空白,使我的叙述连贯一致;但我不愿这么做。我只想记下从亲见亲闻中了解的情况。
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小说,取名《月亮与六便士》。那本书我写的是著名画家保罗•高更,我利用小说家的特权,设计许多情节,来描绘我创作的这个人物。创作的依据,只是我对那位法国艺术家生平事迹的少许了解提供给我的联想。写这本书我却不愿如法炮制。我不会做任何虚构。为了避免在世者感到难堪,我为在这个故事里扮演角色的人自行设计了姓名,我还另外花了心思,确保没人能识别他们的真面目。我写的这个人没什么名气。他很可能永远都寂寂无名。也许在他行将就木时,他的尘世之旅所留下的痕迹,不会多于投石于河水时在水面留下的涟漪。所以我这本书,如果终究有人读的话,只是因为它可能拥有一些内在的趣味。也有可能,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性格中异乎寻常的力量与美好,会对他的同胞施加不断增强的影响,使得大家在他辞世许久以后,或许会认识到,在这个时代出过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到那时,我在此书中写的是谁,就会大白于世,那些想对他早年生活至少有所了解的人,就可以从此书中多少得遂所愿了。我想我这本书,在其得到公认的范围内,对我朋友的传记作者而言,会是用得上的资料。
我不想哄骗读者,说我记录的对话,可以当作逐字逐句的实录。我从不记录人们在这个场合或那个场合说了些什么,但只要谈话与我有关,我的记忆力是可靠的,虽然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这些交谈,但我相信表达的意思不会走样。我刚说过我不做任何虚构,现在我想把这个声明改一改。我采取了自希罗多德时代以来的历史学家惯用的擅自主张,把我本人没有亲耳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讲话,通过故事中那些人物之口说出来。我这么做的理由,跟历史学家一样,都是为了活跃场景,使之逼真。那些交谈,如果只是记流水账一般转述出来,可读性就差了。我希望自己的书写出来有人读,我想,设法提高作品的可读性,是站得住脚的。聪明的读者自有慧眼,很容易看出我在何处用了这种手法,并且完全可以弃之不顾。
我动笔写这本书时忐忑不安,另有一个原因,即我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美国人。了解人是很难的事情,我认为除了本国同胞以外,所有人都是无法真正了解的。男男女女不仅仅是他们本身,还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地域,是他们在其中蹒跚学步的那座城市公寓或那个农场,是他们在孩提时代所玩的游戏,是他们偶然听老太太讲过的故事,是他们所吃的食物,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是他们阅读的诗章,是他们信仰的神灵。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成为现在这样,而这一切不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就能了解,你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才能懂得。你只有变成他们本身才能懂得。由于你只能通过观察才能认识不同国度的人,所以你很难在书页之间可靠地将他们描写出来。就连亨利·詹姆斯那么眼光敏锐、心细如发的观察家,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之久,也未能创作出一个地地道道的的英国人。至于我自己,除了几篇短篇小说外,从未试图描写本国同胞以外的人。我在短篇小说中冒险逾越雷池,是因为在短篇小说里处理人物时可以粗放一些。你给读者画个大致的轮廓,让他们去填充细部。有人会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成英国人,为什么不能将本书中的人物如法炮制呢?回答很简单:我办不到。我一改,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不敢冒称他们是美国人自己眼中的美国人,他们是英国人眼中所见的美国人。我没有试图重现他们讲话的特色。英国作家试图重现美国人讲话特色时造成的乱像,跟美国作家试图重现英国人所讲的英语时造成的乱像是旗鼓相当的。俚语是个大陷阱。亨利·詹姆斯在他写的英国故事里老是使用俚语,但从来不如英国人用得那么地道,所以他非但没有取得追求的对话效果,还动不动就令英国读者受到难过的惊吓。
在威廉·萨姆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我着手翻译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刀锋》(The Razors Edge),而我听说他的另一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的译本正在全国畅销,其第三部代表作《人生的枷锁》中译本也卖得不错。毛姆的长篇小说在中国走红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在世时,就以作品首屈一指的畅销而令其他作家妒忌得眼红,因为他是享有“莎士比亚之后第一人”盛誉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因为世人认为“只有英国作家萧伯纳可以与之比肩”,因为他是一条“趴在百万畅销量之上的老鳄鱼”。在中国,毛姆作品受到欢迎的还不止是他的长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就在我翻译《刀锋》的过程中,也再一次受到中国读者的热捧,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可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媲美,因为毛姆在20世纪的英国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据我所知,尽管《月亮与六便士》的中译本早已问世于我国,但毛姆作品中译文的大量出版,是在我国文化政策较为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那时随着一大批毛姆作品中译本上市,读书界形成了一股毛姆热。作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作家,毛姆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占据了应有的位置。
如今在我国出现第二波毛姆热,其中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就是《每日电讯》报资深记者赛琳娜·黑斯廷斯所著的《毛姆传》中译本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隆重登场。
这部传记告诉我们,毛姆在文学史上有三个令人嫉恨的优势,很多同行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的一生太富有、太多产、太畅销,而他不懂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却要“愤世嫉俗”、“玩世不恭”,所以他很难在学院里找到“一流的位子”,庙堂中人企图把他贴上“通俗作家”的标签,将之压制于江湖之中,不让他跳跃龙门。不料文学之乡法兰西却对他青睐有加,给他以莫泊桑所享有的那种崇高的评价,所以到了1952年,他本国的牛津大学不得不给这位颇以“通俗作家”为荣的作家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称号,而在1954年毛姆八十寿诞的时候,英国人又授予他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
毛姆本人在私生活中的离经叛道,也使英国的正统社会将他视为异类,而在法国,他的人生却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特德·摩根,另一本《毛姆传》的作者,对毛姆评述道:“毛姆是下述一切的总和:孤僻的孩子,医学院的学生,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放荡不羁的巴黎浪子,伦敦西区的成功戏剧家,英国社会名流,一战时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同性恋者,跟有夫之妇私通的有妇之夫,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二战时的宣传家,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其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
部分是由于毛姆的上述形象,尽管他在生前终于得到了本国文坛的承认,但英国的精英未必喜欢他,因为英国文坛的承认,是被毛姆名声在外所逼迫的。他们有理由认为,毛姆的作品不够庄重,不够典雅。那么,在那些不在乎庄重与典雅的普罗大众眼里,毛姆是否就成了他们的偶像呢?非也。尽管毛姆以“通俗作家”而自豪,普罗大众却未必对他着迷,因为他那辛辣犀利的嘲讽和俏皮的幽默还不够浅显不够滑稽,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通俗还“悬在半空之中”,无法令普罗大众捧腹。那么,是什么人为毛姆而狂热呢?应该是中产阶级人士。靠着自身打拼而成功的颇有见识的中产阶级,以其天然的秉性而言,是会觉得毛姆很对脾胃的。中产阶级喜欢他对人性的探索,对宗教的追问,对善恶的吹毛求疵,对情欲和爱情的怀疑,对风俗的喜爱和尊重,以及对贪生怕死的悲悯。毛姆的这些特点,比较集中地反映于《刀锋》中的主人公莱雷身上,部分地反映于男配角艾略特身上。莱雷对人生真谛的求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姆本人的灵魂之影,所以文学评论界将《刀锋》定位为毛姆的代表作。
毛姆的写作手法,也具有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很多作家写人性,借助于情节的起伏和高潮,借助于描写的煽情和催泪,或者借助于对白的雄辩与剖析,例如法国的雨果,例如奥地利的茨威格。但毛姆是不同的,他骨子里是一个英国作家,因此他更像莎士比亚,更像狄更斯,更像萧伯纳,而他在法国作家群里更喜欢莫泊桑,所以尽管他写的是人性,是对道德的探讨,对人性的追问,但他不是咄咄逼人的,他的笔锋是冷静的,他将终极的思考、追问和怀疑,散布于人物的故事中,平铺直叙,娓娓道来,其中的冷静和俏皮,犹如一道精致的美餐,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欣赏理智和冷幽默的中产阶级人群。所以,站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节点展望一下,我们可以相信,在中产阶层日益崛起壮大的中国社会,可能会出现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毛姆读者群。
毛姆在中国受到欢迎是一种现实,是一种推测,也是一个历史的种因。毛姆喜欢中国。在他于1920年访问中国之前,他对中国是好奇的,在他访问中国之后,他对中国有了感情,但好奇之心依然没有冷却,就像毛姆在《刀锋》中所说的,尽管他见过许多大世面,但他对主人公莱雷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东方文明的魅力,东方人民的身影,始终出现在他的笔下。莱雷对印度文化的体验,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在《刀锋》的故事中始终是一种魅力。书中对轮回和得道的探讨,更能拉近和东方读者精神上的距离。毛姆与东方包括中国的渊源,是其作品在中国再掀热潮的一个潜在因素。
毛姆生于1874年1月25日,卒于1965年12月26日,享年九十一岁。作为一位英国作家,他出生于巴黎,逝世于法国,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说明他对法国感情颇深,说明法国文明特别是文学艺术对他的滋养。我们从《刀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巴黎和里维埃拉等法国城市的描写信手拈来,有枝有叶,令人读来情趣盎然,正是因为他有法国的生活与情感经历作为基础。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基本结束,我们无法看到他对战后欧美社会的描述,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译者囿于水平,译文中难免错讹之存在,亦或有未能圆满反映原作精神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以俾改正后交付再版,在此先致谢忱。译者通联方式为QQ号7000901,及电子邮箱7000901@qq.com。
王纪卿
2016年3月14日
于长沙望月湖畔听雨轩
剃刀锋利,越之不易;
智者有云,得渡人稀。
——迦陀奥义书
如果我让读者觉得埃略特·坦普尔顿是个卑鄙小人,那就是我对他不公了。
首先,他是法国人所谓的serviable,就我所知,英语中没有一个词与它的意思完全相当。辞典告诉我,英语的serviceable,作“对人有益”、“乐于助人”和“好心”解时,是过时的用法。埃略特正是这样的人。他为人慷慨,虽然他在入世之初,给熟人大量赠花、送糖、派礼,无疑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但是,当已经不需要再送的时候,他还在这么做。赠与给他带来愉快。他很好客。他的大厨可以跟巴黎的任何厨师媲美,在他的餐桌上,保准会给你上当季最早的时鲜。他的葡萄酒表明他是个品酒的行家。不错,他挑选宾客时最看重其社会地位,意气是否相投是次要的标准,但他会留心至少邀请一两位具有娱乐能力的宾客,所以他的聚会几乎总是令人开心的。人们背地里嘲笑他,说他是下流的势利鬼,却照旧欣然接受他的邀请。他的法语讲得流利正确,腔调无可挑剔。他煞费苦心地学习英国人如何讲英语,想要从他的讲话中不时听出一点美国调子,你的耳朵要非常灵才行。只要你不跟他谈起有关公爵和公爵夫人的话题,他就非常健谈。但即便是谈到那些权贵,既然他的地位现已巩固,他也会容许自己妙舌如花,在你跟他单独交谈时,他就更加没有顾忌了。他有一根快活的毒舌,而有关这些显贵要人的丑闻,无不钻进他的耳中。我从他那里得知谁是某王妃最小那个孩子的父亲,谁是某侯爵的情妇。我相信,就连马塞尔·普劳斯特掌握的贵族秘闻,也多不过埃略特·坦普尔顿的知识。
我在巴黎居留期间,我们常常共进午餐,有时在他的公寓,有时去餐馆。我爱逛古玩店,偶尔买件古玩,更多的时候只是观看,而埃略特总是兴致勃勃地陪我去。他懂行,并且真爱艺术品。我觉得他熟悉巴黎的每一家古玩店,而且和老板混得很熟。他热衷于讨价还价,我们出门时他老是对我说:
“你看上了什么,不要自己去买。只要给我暗示一下,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办。”
当他以开价的一半为我买到想买的东西时,他会兴高采烈。看他和卖家讨价还价是一种享受。他会争辩,劝诱,发火,要卖家讲讲良心,嘲笑卖家,指出那件东西的毛病,威胁说不再踏进这家店门,叹气,耸肩,训话,皱起眉头气冲冲地朝门口走去,当他最终砍价成功时,他会伤心地摇头,仿佛他乖乖认输了。接着他会用英语对我耳语:
“买下吧。比这价钱再高一倍,也算便宜。”
埃略特是个热心的天主教教徒。他到巴黎没住多久就认识了一位法国神父,此人因为劝说不信教的人和异教徒皈依教会而闻名。这位神父是个宴会狂,并且机智过人。他只为有钱人和贵族服务。不可避免地,埃略特会被此人吸引。此人虽然出身卑微,却能成为那些门禁最严府邸中的座上宾。埃略特曾向新近接受这位神父劝告皈依天主教的一位美国阔太太透露,虽然他的家族总是信奉圣公会,但他早就对天主教会感兴趣了。一天晚上,美国阔太太请埃略特在餐桌上会见了这位神父,就他们三人在场,神父谈笑风生。埃略特的女主人把谈话转向天主教的教义,神父讲得虔诚,但没有卖弄学问。他虽然身为神职人员,但他是作为尘世一员对尘世另一员讲话。埃略特荣幸地发现,神父对他的一切无所不知。
“范杜木公爵夫人前几天还谈到你。她告诉我,她认为你智力非凡。”
埃略特高兴得脸红了。他经人引领见过那位殿下,但他绝没有料到,殿下竟然没有把他立即忘掉。神父谈到信仰,讲得既聪明又和气;他思想开明,观点新潮,胸怀宽容。听他一席话,埃略特觉得教会就像一家高级会所,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是非加入其中不可的。半年后他被接纳到其中了。他的转变,加上他对天主教慈善事业捐赠时表现出来的慷慨,为他打开了过去对他关闭的几扇大门。
他放弃祖辈的信仰,可能怀有不纯的动机,但他改教后的虔敬是无可置疑的。他每个星期日都去上流人常去的教堂做弥撒,按时去忏悔,并定期访问罗马。终于,他的虔诚得到奖赏,他当上了罗马教皇内侍,而他执行公务的勤勉尽职也得到了奖赏,他可能是获得了圣墓神职。他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的事业,事实上跟他作为homme du monde即俗人的事业一样,取得了同等的成功。
我常问自己,是什么导致如此聪明、如此善良、如此有教养的一个男人被势利迷住心窍呢?他不是暴发户。他的父亲在南方一所大学当过校长,他的祖父是个有点身份的牧师。埃略特那么聪明,不会看不出许多接受他邀请的人,之所以应邀前来,只是为了吃免费餐,而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很笨,有些人毫无价值。他们响亮头衔的魅力使他看不见他们的缺陷。我只能猜想,跟这些古老世家的绅士混得很熟,成为其夫人的忠实侍从,给了他一种绝不会厌烦的成就感;我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激情的浪漫主义,致使他在羸弱瘦小的法国公爵身上看到了曾经跟随圣路易前往圣地的十字军骑士的影子,在那些猎狐时大呼小叫的英国伯爵身上看到了曾经跟随亨利八世奔赴金布之域的祖先的身影。待在这样的人身边,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辽远而英武的过去。我想,在他翻阅《哥达年鉴》时,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令他回忆起古老的战争,历史性的攻城略地,著名的决斗,外交的谋略,以及国王的风流韵事,这时候,他的心跳便会加快。总之这就是埃略特·坦普尔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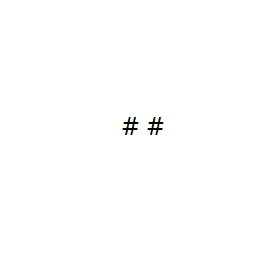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