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夏之白解敏的现代都市小说《全章节阅读爆改大明》,由网络作家“一两故事换酒钱”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长篇小说推荐《爆改大明》,男女主角夏之白解敏身边发生的故事精彩纷呈,非常值得一读,作者“一两故事换酒钱”所著,主要讲述的是:穿越大明洪武年,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新青年。身处明朝腐朽的旧社会。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么爆改大明,要么为旧社会爆杀。宁为乞丐,不为家奴。以科举涉足,以眇眇之身,撼天动地。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21世纪新青年,见帝不跪,天策状元,翰林大学士,礼、户、兵、工、刑、吏六部尚书,华夏最后一位宰相,古往今来最有权势的摄政王----夏之白!...
《全章节阅读爆改大明》精彩片段
郭翀等官员心神一凛,连忙起身,去到一旁空处,跪伏在地,恭迎着太子朱标的到场。
很快,穿着一身常服的朱标,进到了殿内,朱标一脸方正,面色略显削瘦,嘴角带着温和的笑容。
入殿。
见诸大臣尽皆跪伏,朱标眉头一皱,不喜道:“众卿快快请起,我大明自洪武四年起,陛下便已下诏,诏定官民恢复揖拜礼。”
“旧元之胡俗,大明已废除了。”
李善长在一旁抬手,示意殿内官员快快起身,同时道:“殿下所言极是,陛下驱除鞑辱,恢复中华,在立国之初,便决意推翻元朝人一切。”
“立国时,天下军民行礼,尚还遵循着胡俗,饮宴行酒,也多以跪拜为礼,故我大明选择陈刚立纪。”
“不过百官之所以对殿下行跪拜之礼,臣以为非是遵循胡俗,而是遵循着我大明另一条律令。”
“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禀事则跪。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行跪拜礼。”
“殿下这次为陛下任命为科举阅卷的总裁官,为我等臣子直属上司,自当受此跪拜之礼。”
李善长作势朝朱标一礼。
郭翀等人也顺势,顺着李善长的话,朝朱标作揖行礼,眼中对朱标还流露着些许的感动。
朱标摇摇头,也没再说。
李善长微微一笑,眼中露出一抹狡黠跟精明。
他知道朱标并不是真的厌恶百官行跪拜礼,而是今日阅卷的官员,多是有文采有才能的人,朱标对这些人向来看重,所以才会特意说一句,也表露自己的尊重跟亲近。
李善长自是明白其中道理,所以才特意开口替官员解释了几句,也顺便给了朱标一个能接受的理由。
两方都得了体面。
大明名义上的确废除了旧制,但书面上跟实际,终究还是不一样的,若是真信那些,只会害了自己。
这次被征来阅卷的官员,都在朝中任事有十几载了,哪还有人不知其中的规矩。
朱标坐到主座,沉声道:“我朝上次科举距今已有十三年,如今科举新开,参加科举的举人很多,而今试卷都已密封在此。”
“孤也不多废话。”
“就一个要求,诸卿切莫生出徇私舞弊的心思,公正阅卷,对所有考生的试卷都要一视同仁。”
“若是有人存了私心,破坏了科举的公正,败坏了我大明的名声,那就莫怪孤不留情面了。”
朱标一脸冷峻。
他绝不容许有人在科举阅卷上弄虚作假,谁敢败坏大明科举的公正性,他决不会留情。
李善长等官员连忙道:“臣绝无私心,定会禀公阅卷,请殿下放心。”
朱标颔首。
他挥了挥手,示意一旁的小吏,将这次科举的试卷分发下去。
这个小插曲后,文华殿再度安静下来,众官员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审阅起被分配到的相关试卷。
期间,若有试卷出众,便会通报给其他官员知晓,做标识,等初审完毕后,则会交由其他官员再度审阅。
继而确定最终名次。
临近晌午。
吴公达已审阅了近百份试卷,只是入其眼的屈指可数,这些试卷其实未尝没有亮眼之处,只是不够。
破题、承题、起讲、第一股、第二股、第三股等到收结,并不能一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科举这般盛大考试中,不能始终维持亮眼回答,终是成色不够,也不足以支撑起这名考生脱颖而出。
就在吴公达新翻开一份试卷时,只是粗看,却不由眼睛一亮,随即高声念了出来。
“禀殿下,我这看到了一份不错的试卷。”
“会试第一考,考题: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而这名考生的破题,承题都颇有见解。”
“这名考生的破题观点为: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而后的承题为: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
“……”
吴公达一脸肃然的将这篇答题念了出来,以征求其他大臣看法,若是得过半大臣认同,则能列入下一步审阅的流程。
朱标等人认真的听着。
会试第一考内容的题目出自《论语·颜渊》,考的是百姓跟君主的关系,而吴公达念的这篇颇有文采。
论述论据都言之有理。
可谓出彩。
就在吴公达神色喜悦的念到第五六股时,只听扑通一声,旁边的郭翀却一个不留神掉下了凳子。
这一幕也是引得众人大笑。
吴公达被这一打断,也是下意识停了下来,不过后续念不念完已不重要了,他方才注意过朱标、李善长等人神色,都对这试卷很满意。
这篇试卷其实也没必要再念了。
已经达标了。
他收拢试卷,看着郭翀,也是来了兴致,开口调侃道:“子翔兄,这篇试卷所写内容固然不错,但也用不着你这般惊讶吧。”
“你当年科举所写文章,可是被列为会试第一,如今这般大惊失色,可非你寻常本色啊。”
吴公达调侃着,借此活跃了一下场中气氛,临近晌午,马上就到进食的时候了,自没必要那么严肃。
然而郭翀没有接话。
也难得的没有出声反驳,他两耳好像根本没听到吴公达的调侃,双眼直勾勾的盯着眼前试卷,脸色毫无征兆的变得煞白。
嘴唇更是发青,身子也不住的颤抖起来,瞳孔间充斥着恐惧,根本没有吴公达以为的半点欣喜之色。
只有恐惧。
他看到了一篇反文!
朱标也笑道:“郭侍郎,你的才华孤还是有所耳闻,这篇试卷答的是不错,但这毕竟是停了十几年科举后的再开,在这些年,自然也是积累了不少文人志士。”
“为何会这么失态?”
郭翀如梦方醒,根本顾不得擦拭额头冷汗,也没有起身,直接跪伏在地,颤巍巍道:“禀殿下,臣并非失态在吴兄念的那篇试卷,而是……”
“而是臣自己看的这篇。”
“哦。”朱标目光微异,也是来了兴趣,笑道:“可是又有大才为爱卿发现了,快,念给孤听听。”
朱标一脸欣喜。
大明重开科举,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从天下挑选治国大才之人吗?如今一篇试卷竟能惊的一位榜样大惊失色,这如何不让他惊喜?
郭翀低垂着头,根本不敢抬头,更是支支吾吾不肯言,直到朱标再三追问,这才颤巍巍的开口。
“回殿下。”
“臣看到的不是什么大才之文,而是一篇……”
“反文!!!”
夏之白的话一出,四周瞬间安静。
前面出声嘲讽的丁显,此刻更是脸色惨白,看向夏之白的眼神充满了恐惧跟惶恐。
他们作为举人自是清楚这次科考的变动。
自科举开创以来,历朝历代的科举内容都不尽相同。
唐代主考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
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
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
不过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宋朝便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元朝时,停科举停了很长时间,后续虽有重开,但对于汉人、南人有极大限制。
甚至当时一直盛行一句话‘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这个国人指的是蒙古人跟色目人。
元朝说是举行科举,实则是借科举巩固蒙古、色目人的特权地位。
大明开国以来,朱元璋便重开了科举,科考程式效仿着元朝。
‘五经’而后‘四书’,并保留了唐宋时的‘古注疏’习惯,这时的朱元璋对于传统的‘经术’和‘经史’还十分重视。
只是首开科举后,朱元璋对当时的取士情况并不满意,继而直接宣布废除了科举。
等洪武十五年重开科举,则对科举内容做了极大限制,不仅直接变成了考八股文,还将科考的学术视野局限在了宋代出现的理学观点上。
这个变动从某种程度而言,降低了科考的难度,因而为南方考生认为是朱元璋在有意打压南方学子,以录取更多的北方学子。
这无形间也加剧了南北两地学子间的隔阂跟冲突。
若是陛下的改革失败……
丁显心头念着这一句话,额头冷汗狂冒,已被这几句话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花纶淡漠的看了夏之白一眼,又看向了丁显,满眼鄙夷跟不屑,堂堂举人还能被这些唬人的话吓住?
真是丢他们南方士人的脸。
花纶看向夏之白,眼神正视了不少,只是神色依旧冷淡,道:“朝堂对科举内容做出变动,自有朝堂的考量,我等作为考生,能做的,要做的只是参加考试而已。”
“至于你所说的改革失败与否,跟我等考生有何关系?就算真的改革失败了,那也是朝堂的错。”
“与我等何干?”
“我等本本分分参考,不曾做半点弄虚作假,也不曾徇私舞弊,名次也是朝堂排出来的,还有错不成?”
“若是三甲无一名北人,那只说明了一件事,便是北人的确是烂泥扶不上墙,就算朝廷为此做再多改变,依旧改变不了烂的现状。”
“也彻底证明了北方真的不行。”
“怎么改都是徒劳。”
花纶说话的语调很慢,慢条斯理间却带着强烈的攻击性。
夏之白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北方文脉薄弱非朝夕的事,自元一统天下后,便存在着‘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的情况。
若再往上论,自安史之乱后,华夏的文化经济就已开始偏倚南方,而北地长久的战乱,也严重的影响了学术在北方的传播跟发展。
这也是必然的。
朝夕不保,生计都是大问题的情况下,哪还有精力去研究学问。
若非还有着江汉赵复等南儒有意的北传理学,北方眼下的文化只会更加衰败。
朱元璋一统天下之后,明显察觉到了这点。
故多次颁‘四书五经’给北方,并多次命吏部迁南方学官北上,还特意颁布了南北一致的《大诰》。
只是效果甚微。
朱元璋看出南方文化太强,北方久经战乱,文脉不昌,刻意停了科举十年,让北方恢复。
但夏之白知道,这个所谓恢复太片面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生产水平远低于南方,在这种情况上,就算朝廷给予再多扶持,想在教育跟文化上追赶上南方,也几乎不可能。
再则。
明初其实是个南人政权。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以南方为基础的,特别是大多数官僚都出身江南,这些官员无疑会更加注重南地的地方利益。
朱元璋在一统天下之后,已经在有意压制南人了,但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想真正达到南北均衡,最终还得落在发展北方经济上。
夏之白深吸口气,肃然道:“我等现已为举人,也几乎都会为大明官员,既为官员,自当以天下为己任。”
“若是科举往后只有长江以南的南人,而无长江以北的北人,那岂非意味着大明只有半壁江山。”
“陛下当年起兵时,喊的口号便是驱逐鞑辱,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恢复中华,难道恢复的只是长江以南,而不包括长江以北?”
“长江以北久经战乱,的确各方面都比不上南方,但恢复北方生产生活,不当是大明官员该致力的事吗?”
“当今陛下之所以致力改革科举制度,便在于你们这些南方学子,毫无天下之念,只有一己私心。”
“甚至还以贬低北方为乐。”
“尔等自诩满腹经纶,却是连这点道理都通晓不得,当真是枉读了这些圣贤书。”
“你们的这番言语,更是让我坚定了成为状元的信心,因为我有了不得不成为状元的理由。”
夏之白语气很平淡,冷静的仿佛在说一件早已确定的事。
花纶冷哼一声,没有再反驳,也不能再反驳了,只是冷声道:“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十天后,再来看看,这会元会落在谁头上。”
“希望到时你的嘴,也有今天这么硬。”
夏之白摇头,露出两排白皙的牙齿,笑着道:“你又说错了,我不是会元,而是状元。”
“另外我若是当状元,跟历朝历代的状元都会不同。”
“我这状元将会是天策。”
“也是古今唯一!”
“天……”花纶刚想出身,状元何曾有过天策的头衔。
随即却是想到了另一个跟天策有关的称号,脸色腾地巨变,看向夏之白的眼神满是骇然。
心中更是暗骂不已。
‘天策’二字是能随便取的?
古往今来只有唐太宗获得过天策上将之名,这还是因为当时军功实在太高封无可封,这才得此殊荣。
你夏之白何德何能敢有这野心?
这是找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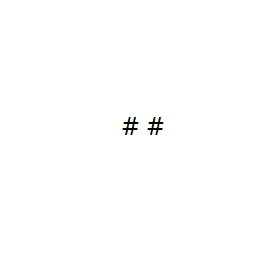
最新评论